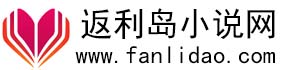110-120(14/27)
,头歪向内,两道灼热眼泪便淌了下来。太监们问他时,他说自己是着了怜妃的道儿, 什么都记不得,也弄不清楚了。整个人都如坠云中,恍恍惚惚。太监们连声应着,是了, 就是如此,殿下是中了邪,这回司礼监请了几位高人做法, 定要将那狐媚子驱逐宫外,还皇宫一个清净。可待众人都走后, 太子却哭了。他哭得伤心欲绝,因为他听人说,怜妃死了。
他到底是真心爱着她的, 虽说这一情感一开始出自于色欲以及隐隐的仇恨, 可到最后这爱也是真实不容置疑的。哪怕在最后一刻,她的微笑暴露出了某种他一生都无法知晓的目的。
可在那一刻,那一刻……萧裕隐忍地哭泣, 他竟是愿意同她一起堕入地狱的。
昔人已逝,独留他苟延残喘。作为东宫之主他是不配的,作为一位情人他亦是失败的。再多外界的声音他也听不进去了,哪怕张邈等人如此作保,护他在东宫之位上无忧,可他也不在乎了。
也许,他累了。
守住这个位置,已经让他成为了另外一人,他从不认识的萧裕了。
可这个位置哪里又独独是为自己而坐的?
众藩王、众大臣,往日里仰仗他而得势的,为了保住自身地位和利益,架也要把他架上去。他是招牌,是保证,是傀儡,亦是工具。
张邈拢了拢衣袖,转身,在暮色苍茫中,他深深回望了一眼东宫。
是夜张府中,张邈踱步在书房。
“您要我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?”书案前,年轻人在灯下翻阅一本书。此话似乎不是对张邈说的,而是自言自语。
“你已有决定。”
“那是您所希望的吗?”
“也许罢。”
“我并不值得人信任。”
“没有人值得信任。”张邈走到窗前,“我已经能看到脚下道路的尽头,但属于你的,也许才将将开始。”
“我该怎么报答您?”
张邈微微一笑,不做回答,只是道:“人都论官有清有佞,实则为官无清无佞,无非都是相争,为君父办事。今日君父要你奸,你就奸,要你清,你就清。什么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,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。这沧浪之水都养了两岸田地,清与浊无非都是表面。我张邈担了这大宁朝第一奸党,已不求什么身前身后名。你作为我唯一亲近之人,你知道我是个什么人就好。”
“阁老……也许……”年轻人动容。
张邈摇了摇头,“没什么也许,也许从不存在。”
烛光摇曳在他苍老的眼眸里,恍如二十年多前的那场熊熊大火。漫天的火光中,他被推开,被置身事外。林可言交托给他的,他终没能办到。
因为张云深就是如此平庸的一个人,无数次他对自己说,张云深平庸至极,辜负了林可言,他因为恐惧屈从于皇帝威压之下,被撕裂,被掌控,被迫沦为了皇权的工具,成为权力斗争的中心。他没能扶持好大宁朝,这个国家在他手中一路下滑,如今他再也难以为继。
若不是林安晚的出现,他依旧会扮演好这个角色,直待结束。
若不是林安晚执意要活,他将仍然是那个高高在上,不动声色的张首辅。
所以他,好似回来了,他要亲自改变。
那么自己,还能再度置身事外吗?
转身,落寞攀附于心,张邈伫立于窗前。夜色寂寥无光,像极了他的一生。
——
风吹夏荷,程菽转身,不知何时宋步苒站在了他的身后。
“我这些天一直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