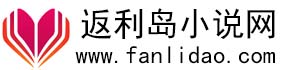13-18(18/37)
耸动的纤薄肩骨,拘谨地拢高、拱起。能看得出,也在紧张。
显然这样的坦诚对彼此而言,都是某种情感和道德的考验。
伦理身份的拉扯,在天然的年龄差面前溃败。
他知道分寸,知道进退。
知道什么叫“清者自清”。
心如明镜,不生不灭,不垢不净。
耳后,是铝管药膏的盖帽被扭开的细微声响。
周予然低低垂着头,将拢在身前的衣服往胸前又拉了拉,尽可能挡住春光。
温热的指腹带着很凉很凉的冰片薄荷软膏轻揉上后背,发挥药效的涂面再次让理智降温。
周予然忽然有点后悔,刚才下车的时候不应该关掉音乐。
车里太安静。
安静到任何一丝情绪都被无限放大。
谢洵之肯定不喜欢这样。
太急于求成,难免被看出道行浅。
他应当在心里怪骄作、不知进退。
指不定明天就要借故跟保持距离。
这次会去哪里?
瑞士、澳洲还是纽约?
又要去多久?
如果他真这么做,那么“男妈妈”和“男朋友”这两个档,一个都别想读。
一种游戏机被没收的无力感,让原本因为紧张而耸起的肩胛骨下落,连肩膀也颓唐地拉耸下来。
“还难受吗?”
幽闭的车里,男人微沉的声音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酥麻感,熨帖在耳膜上,痒意顺着血管像毒虫爬进心里。
忽然觉得,其实一开始就没得选。
早就病入膏肓。
之前预设好的两个存档,贪心——
都要。
“好多了。”
周予然咬着下唇,搜肠刮肚不知道该怎么确认他此刻情绪——是负面,还是极端负面?
但身体已经先情绪一步放松了下来。
沉默再次蔓延。
有柔软的膏体被涂抹在发痒发麻的皮肤上。
男人饱满的指腹带着薄茧,摩擦在后背的小红疹上时,能感受到明显的磨砂感,但这种磨砂感,在软膏的缓冲里,又被来回地润了又润。
仅有微弱阅读灯的环境下,视野朦朦胧胧,像罩了一层柔光的纱。
裹着软膏的手指,顺着蜿蜒纤薄的脊椎骨往下,却委顿在了衣料松垮堆叠的腰间。
他太久没动作。
周予然闭上眼睛,将脑袋靠在车玻璃上,冰冷的纤维面让昏昏涨涨的脑袋变得更加清醒。
“有什么想问的可以直接问。”
腰上有个纹身。
距离左侧腰窝两指宽的地方。
S&S。
宋叔叔和予然。
“什么时候弄的?”
避开纹身,他再次从铝管里挤出一截药。
“7月2号。”
没讲具体哪年,但他知道,这是他三年前离开宁城的第二天。
视野里的空气升温似乎到了某种极限。
嫩白的荔枝果肉被放进高温的牛奶里煮,咕噜咕噜地冒着泡泡。
香得有些要命。
像绞刑架上悬空的绳索,似乎已经量好了他头颅的尺寸。
“纹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——”
不管我躲到哪里,我就偏不如我的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