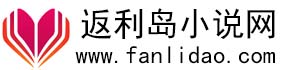30-40(18/60)
着把她送到了阿椿和阿榧房间里,吩咐两人好好照顾她,又去驿站各处检查了下,等各处都安顿好了没有发现问题才回到姜从珚房间。一夜安宁。
第二天,中途歇息的时候,姜从珚却收到一个消息——
文彧病了。
她思索了下,让若澜带张复去给他瞧瞧,张复看诊完回来禀告,神色有些古怪,“文大人的病不是病。”
姜从珚抬了下眉,静静等着他的下文。
张复继续说:“文大人一直说头疼,没有力气,我把脉时并无异样,或许是旅途劳累所致吧。”
旅途劳累也不是这个表现,这些日子他给好些人看过病,有水土不服的,有身体虚弱的,他都能诊出来,可那文彧,自己瞧着分明没有问题,他却非说难受。
张复觉得他在故意装病,却不好当面拆穿,只能回来禀告女郎。
姜从珚听罢,脸上却露出一抹松快的笑,眉眼晕出动人的眼波,肤色如雪,在浅浅的春阳下明媚如绽放的牡丹。
张复不经意瞧见,也觉女郎过分美丽了。
他跟在女郎身边好几年,见过她无数次,两人甚至经常探讨新医,他已经对她十分熟悉了,可总也还会被她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清丽之姿惊艳。
最平常不过的动作,由她做出来偏就有种旁人难以比拟的美丽,不仅仅是五官的美丽,更多的是一种浑然天成的气韵,这是旁人模仿不来、书画也无法描摹的气质。
因而成就了这倾国之姿。
张复恍了下神,然后就听她说,“既然文大人病了,那就让他好生养病歇息吧。只是随行的宫人和匠人颇多,事情繁杂,恐他没精力处置,如他愿意的话,就让若澜去暂管一段时日吧。”
张复听到这话,猛然意识到什么,瞪大眼睛看着她。
姜从珚却只他对无声笑了笑,仿佛一切尽在掌控中。
若澜去看望文彧,很快回来复命,脸上同样带着喜意,“女郎,文大人已经同意女郎的安排了。”
姜从珚低眸浅笑,“他呀,是个聪明人。”
不然她怎么会在离京前特意让父亲把他安排到送嫁队伍中来呢?
看主仆俩配合无间,只有张复还停留在震惊中。
难道女郎从一开始就在谋划这件事,而文彧装病也是在配合她?
可一路走来,女郎和文彧都没说过几句话……
“你们在说什么?”
一道低沉威严的男声陡然插进来,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大片阴影。
姜从珚眼前一暗,抬头一看,是拓跋骁。
正值中午,队伍刚走出山路,眼前是一片绵延起伏的草原,众人停下车马修整用饭,姜从珚也出了马车舒展僵硬的身体,此时正坐在兕子铺好的白色羊毛毯上,刚用完饭、喝了茶。
她的位置太低,男人身量太高,她仰头看去也只瞧见他凌厉的下颌线,也不知是不是背着光,他面色似乎不大好,有些晦暗。
不过姜从珚没放在心上,也不起身见礼,就这么坐着朝他笑了笑,娇声说,“王,您来啦!”
她慢慢发现,只要自己叫他“王”,尤其是语气再软一点的时候,男人就像被挠了下巴的猫猫,一下子愉悦起来,或许男人都吃温言软语这一套?
果然,听到她的声音,拓跋骁的脸色瞬间好了不少,瞥了眼她身下的毯子还有余量,一屁股坐到她旁边。
他刚刚在湖边给爱马洗完澡梳完毛,转头便看到她对着别人的男人笑得灿烂极了,这个男人瘦小不堪,可一张脸勉强算得上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