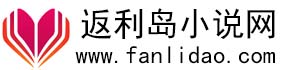170-180(4/54)
着胡须:“女郎现在的情况确实有些凶险,结果如何,还要看女郎自己的心智,我只能扎针辅助疏解。”“还不快扎。”拓跋骁催促。
张原瞥了拓跋骁一眼,“下针需要屏气凝神,漠北王心绪激动,不如暂避片刻吧。”
拓跋骁不肯动。
张原便也不动。
两人对峙片刻,终究还是拓跋骁败下阵来。
他离开床边,却没出屋,只站到了一边。
张原从药箱中取出银针,选了数根,仔细消过毒,让兕子掀开姜从珚身上的被子,又给她解开大半衣裳,对着她胸口连下数针,又稳又快。
她此时的气息确实微弱,胸口出几乎没有太大起伏。
下完针,张原又给她把了一次脉,待时间差不多了才收针,与此同时,姜从珚的呼吸似也比刚才顺畅了些。
拓跋骁眸光一动。
扎针只是辅助理气,张原又让人将军医开的药方拿过来,看了片刻,重新写下一张方子,让随行的弟子去抓药熬药。军队出发得急,只带了些常用急救的药材,不如他准备的全面。
又发现姜从珚身上许多擦伤,问兕子给她上了什么药,兕子将药粉拿出来,张原嗅了嗅,猜到这是大儿子张复制的,“还成,暂时先用着吧,一日两换,等后面结痂后我再重新配一个。”
处理完这些,他看向拓跋骁。
以张原的眼力一下就看出他伤势有多重,寻常人只怕早晕过去了,偏他靠着超乎寻常的毅力竟能撑到现在。
作为医者,行医多年看得多了后,他深觉“人”的奇妙,有的人郁郁寡欢,一个小小的风寒就能要了性命,有的人重伤濒死,靠着一口气硬是在阎王面前打了个转又回来了。
所以,医疾也是医心。
张原起身来到拓跋骁面前,“您也治治?否则女郎好了,您却见了阎王,到时我也不好跟她交代。”
这话实在胆大包天,众人对拓跋骁都战战兢兢,也只有他敢开口。
拓跋骁没理会,只问,“她什么时候能醒?”
张原没好气,“女郎累了这么多日,叫她好好睡一觉怎么了?我看漠北王您也需要睡一觉。”
“我不……”
他刚开口,张原袖摆一挥,拓跋骁只闻到一股强烈的药味,整个人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
固执又不听劝的人,总要用点特殊的手段。
“来人。”张原唤了句。
他让两个徒弟把拓跋骁抬到隔壁房间去,先把铠甲衣裳全扒了,几人这才发现他脖子上还挂着一个结,像是一种平安结,早被血水浸得透透的。
寻常人多半挂在腰上当配饰,挂在脖子上总有种格外的珍视。
张原瞥见,吩咐徒弟不用取,用温水洗去上面的血,再用干帕擦干。
等清理掉拓跋骁身上大部分血污,张原这才给他处理起伤口。
他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块好肉,深的浅的刀伤箭伤,血肉翻飞,胳膊和大腿的肌肉中嵌着几支断掉的箭头,肩上和后背两道伤口见了骨,脖颈处也一道长长的口子,离动脉只差一点,只庆幸拓跋骁战斗经验丰富,没被敌人捅破内脏和大动脉这等要害之处,
但他失了不少血,这些皮肉伤要是不好生处理感染发炎的话也有性命之忧,更不用说他还熬了六七天,同样是在透支。
这些年张原一直在研究姜从珚所为的新医学,对人体的各种解构和微观层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,又一直在军中实践,如今对付各种外伤已经有了一套体系,手下动作飞快,该拔